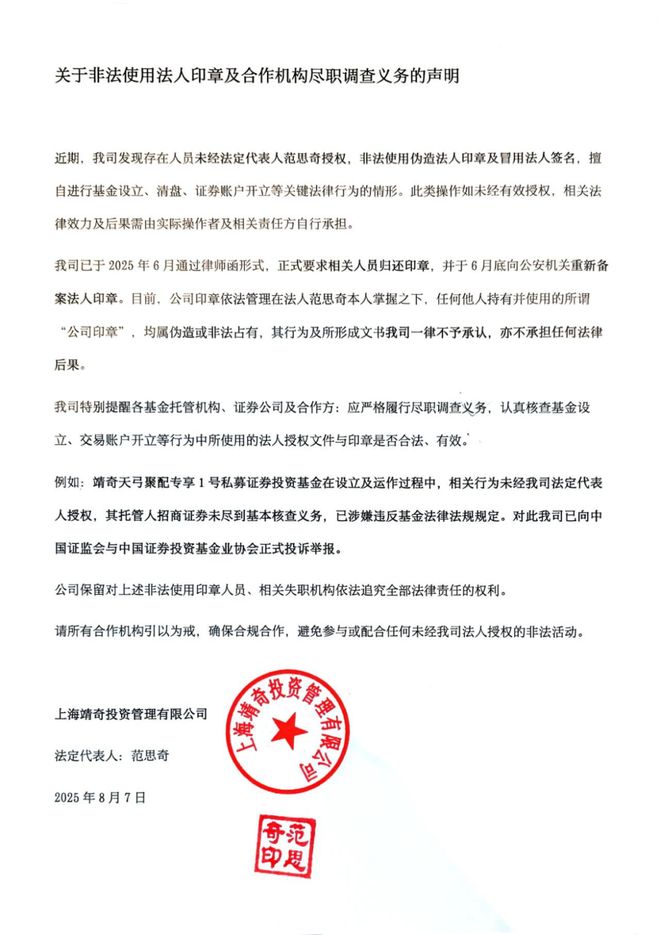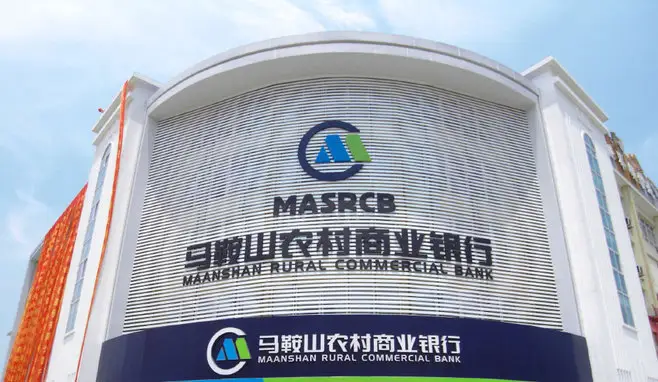一段时期以来,国家对一些具有雄厚实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平台企业进行了重点规制,实施了以反垄断为核心的监管。可以想见,平台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已经广泛渗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一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催生了一个依平台而兴的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概念是舶来品,目前尚缺乏对零工经济的统一定义。“gig”原意为不断切换演出地点,工作机会和报酬具有不确定性的音乐艺人。其实,我国传统上即有“打零工”的说法,主要强调工作的项目性、任务性与临时性,主体多为自由职业者,以随叫随到、以件计酬为特点。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的迅猛发展,近年零工经济的概念逐渐演变为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劳动力供需方的经济模式,以劳动力匹配的按需性和众包性为特点。根据《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县域市场有零工收入的人群占比52.27%,35.11%的县域零工与互联网相关。
国内外不同学科对于零工经济的研究视角各有侧重。社会学主要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内在因素,重视平台控制权、就业者自主权及对平台管理权、组织运作方式的民主参与性;经济学主要关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中不同变量对零工经济各方行为方式的影响;心理学主要关注劳动者内在驱动力,聚焦劳动者从事零工经济的心理需求、工作满意度、工作乐趣和家业平衡等情绪性因素;劳动法学主要关注零工从业者的法律地位,重点讨论零工从业者应享有哪些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
但是,无论从哪个范式与角度去研究,“平台”一定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因为当下之零工经济已经呈现一种“一肩挑两头”的态势——一头是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一头则是零工经济的需求方,而中间则是平台。平台就像一个支点,挑起了零工经济的千钧重担。
起初,“平台”只是一个信息中介,将供需双方的信息交换、撮合,以实现更大程度的信息对称,提高匹配效率。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算法成了平台最重要的内核。算法可以知道快递小哥到哪了,也可以给网约车司机们发送任务单,更可以给平台上的各类参与者打分评价甚至画像,根据评价结果决定后续的派单任务量。更有甚者,有的平台还可以对完不成算法派送任务的从业者予以经济惩罚。一句话,平台通过“算法”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可以想见算法将会在零工经济中取得决定命运的作用。
零工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有两个。
一是,就用工端而言,零工经济是对雇佣关系的重构。零工经济在用工端的重要特征,就是把传统用人单位应该承担的各种成本外部化,由于零工并非建立劳动关系的正式雇员,因此可以免除传统用人单位对正式员工承担的各项责任。零工经济导致的工作任务“碎片化”,意味着用工端对劳动贡献衡量标准的转变,结果导向将取代传统劳动关系的过程管控。
二是,就从业端而言,新生代劳动者职业价值观发生变迁,他们对自由、灵活的崇尚成为零工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环境。可以自主决定工作计划、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成为零工经济吸引新生代劳动者的原因。零工经济同时也转变了劳动者的职业理念,部分人群从过去对“企业的忠诚”开始向对自己“技能的忠诚”和“职业的忠诚”转变。
零工经济虽然对宏观经济有大的贡献,但亦存在工作稳定性低、缺乏职业安全与社会保障等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一、现行制度供给难以支撑新业态的突飞猛进。零工“经济”其实是一种新的业态,即劳动力和资本的新组合形式。既然是新组合,就会面临制度缺乏的境地。一方面,没有制度的规制,新业态可以近乎“野蛮”的增长。“让子弹飞一会儿”的结果,往往是催生了几个市值千亿的行业“巨无霸”。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有学者统计,零工经济的从业人员高达8000多万),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另类”劳动者群体。事实上,我国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与现实意义中的“劳动者”并非一个概念。前者的范围要小很多,主要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人,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企业合同制员工,俗称“正式工”。我们目前劳动法对于“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则完全建立在这一“劳动关系”之上。而对于这些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们,则完全无法享受到我国劳动法给予“劳动者”的保障,特别是养老、医疗、伤残等保险的缺失。显然,没有了法律的强制,资方一般不太会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给快递小哥发工资,也不会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给“专车”司机缴纳“五险一金”。
二、人工智能“算法”进一步强化劳动者的弱势。“算法”在为从业者和客户之间打通信息通道的同时,也把给劳动者套了一个“紧箍咒”。平台通过算法给每个平台劳动者不断派单,计算时间消耗,并通过打分系统给予评价,再根据评价决定未来的工作量,甚至对评价较低的劳动者给予金钱处罚。劳动者虽然与平台无任何法定的人身归属关系,但却落入“算法”这张无形的网。有学者甚至将平台外卖骑手称为“困在算法里的骑手”。可以说,过去的劳动者面对的是雇主的“人脑”的指挥,而现在则面临的是雇主“人脑+算法”的控制,相对弱势更加明显。
三、零工经济从业人员缺乏表达意见的渠道,也难以形成群体力量保护自身权利。一方面,零工经济最大限度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双向选择——劳动力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彰显了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零工经济的运营机制存在民主参与性不够的问题,使得其从业者难以向平台方或者客户方表达意见,因为这些人并非雇主。而从业者自身更像一个自雇者,美国法律称之为“独立承包商”。对于他们,似乎目前亦无类似于工会、行会之组织为其维权,更难形成群体性力量。显然,个体的声音和力量在资本面前都是弱小和无力的。
上述原因中,核心当然是第一点。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制度供给跟上,诸如资本通过对制度解构而“绕”过规制,劳动者自身法律意识不强,执行部门在此问题上态度摇摆等实际问题,均可能构成零工人员劳权难以得到保障的“他项”因素。
据某公益组织发布的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劳动权利现状的调研报告所示,这些“劳动者”甚至面临不知道自己为哪个“雇主”服务的窘境。某公益律师亲自在某知名送餐平台上下载了《服务合作协议》、《众包隐私权政策》、《众包用户协议》等,找遍全文也找不到雇主(用人单位)是谁,只找到了一段长长的“主体信息”,第一句是:“**众包平台经营者是指经营众包平台的各法律主体”。这也就是隐晦地告诉每个签约骑手,你们就是自己的雇主。更有甚者,某些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利用骑手法律知识的不足,与配送商“合作”将骑手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从而彻底将劳动者与平台区隔开来。
对政府而言,面对千万量级的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劳动权利,应尽快为劳工劳动者补齐权益短板,针对性地完善现行制度,通过二次分配促成社会公平的目标,使广大“零工”们早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但如果简单套用现行《劳动法》的劳动基准和社会保障标准,则又重回传统企业用工形态,从而因成本增高使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的效率优势下降,对这一新业态造成打击。
因此,下一步的政策制定在平衡上述两方面问题和利益时需格外小心,以精准的分类将纷繁复杂的零工从业者大军予以类型化,对不同类型的从业者施以不同的保护措施,实现在“分类施策”基础上的“精准施策”。可喜的是,有关部委已经出台了一个初步的政策性文件(即《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平台企业公开涉及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算法,并要求各地放开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相信这会是一个好的开端,未来零工经济发展将步入一个平台发展与从业者权利保障并行的新阶段。
(作者李磊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